内容详情
技术塑造生活:以钟表为例
本文字数:1747
“技术”,正如中世纪的“上帝”一样,已成为我们的“时代精神”。本书从技术与科学、技术与现代、技术与未来等方面深刻剖析技术的含义,是一本揭晓技术本质并有独到见解的科普读物。
《什么是技术》(胡翌霖/著,湖南科技出版社2020年10月版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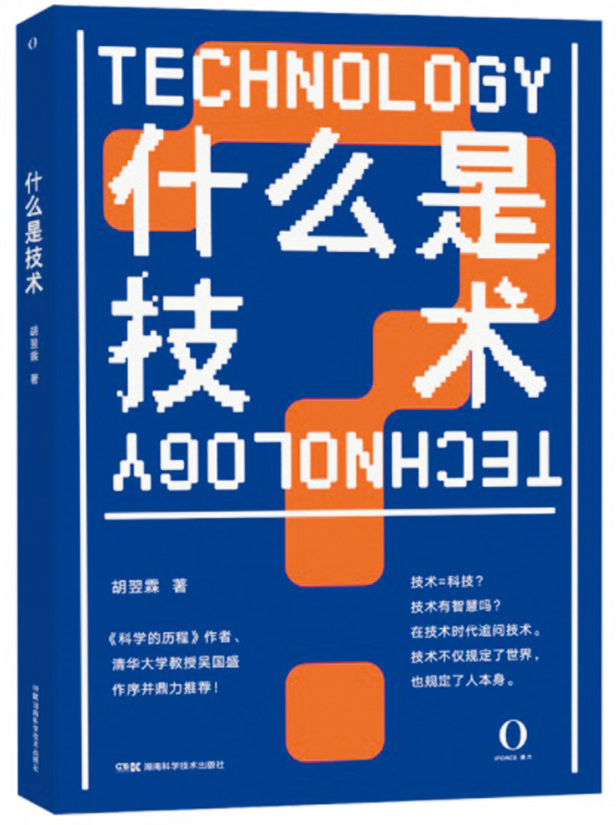
除了椅子,每一种技术或器具都参与着我们生活世界的构成,不但塑造着我们的习俗,也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看待世界的方式。
从每天一睁眼开始,我们就身处技术物的环围之内,我们所认知的时间与空间也都是经由技术转译了的现象。比如说,我被手机闹钟叫醒,从显示屏上读取了当下的时刻,计算着为了准点上班所需耗费的时间。
钟表和手机可以用来“看时间”,这一动作看起来很寻常,但细一琢磨,其实颇为奇妙。首先“时间”这种抽象的东西,竟是可以用眼睛“看”到的;其次,这门技术是有用的,那就是说,我们“需要”看时间。
那么问题来了,我们这种“看时间”的能力和需要是哪里来的?
显然我们并不是每时每刻盯着钟表不停地看时间,我们总是在某些“时机”去看时间。那么,我们究竟在什么时候,需要看时间呢?这个问题本身意味着,在我们看到钟表上的“时间”之前,我们就对“时候、时机”有所把握了。
这句“何时看时间”中的两个“时”是什么关系呢?它们既相通,又不同。前一个“时”更原始,或者说更混杂,它是我们生活中在各式各样的行动和场景中遭遇到的,而后一个“时”则是由钟表这一种特定的技术物呈现给我们的。
在钟表已经司空见惯,已经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世界的每个角落之后,这两个“时”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了,它甚至反过来塑造着我们对前一种“时”的理解。但是在钟表还是一种新奇技术的时代,它的出现和流行,其实是对“时间”观念的一次冲击,一种侵蚀。
我们要回到14世纪的欧洲,最早的机械钟在中世纪的修道院出现了。当然古代就有各式各样的计时工具,但机械钟带来了全新的特点,简而言之,就是它让我们能够“看时间”。古代的“钟”指的是鸣钟,是通过听觉来报时的,西方修道院更早也是依靠打铃。日晷当然也是拿眼睛来看的,但本质上其实还是在看日头,日晷可以说是让我们更精确地“看日头”的技术。而机械钟一方面脱离日月星辰,似乎可以自动运转,因此它给出的“时间”仿佛也是某种脱离一切语境的独立之物;另一方面机械钟给出了视觉的时间,让我们去看、去读。
为什么最早的机械钟是在修道院里流行起来的呢?道理也很简单,因为只有修道士才需要“看时间”。农夫和市民不需要看时间,他们只需要看日头、听打更,他们所需要的时间都是语境化的。所以我们发现西洋钟传入中国的时候也没有被当作一个实用的工具,而是更多地被当作有趣的玩物、工艺品被需求着,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西洋钟都是用来赏玩的,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并不需要“看时间”。
只有修道士需要“看时间”,因为他们建立了一种超越现实生活之外的纪律,他们需要遵循上帝的节奏,而不是任何现实事物的节奏,不是在“日出”或“午后”祷告,而是在“祷告的时间祷告”,所以他们对“报时”的严格性和稳定性的要求,超过了其他世俗生活方式的要求,机械钟对他们而言才是有用的。
很多革命性的新技术,并不是解决了某些需求,而是塑造或生产着新的需求;并不是满足了某些生活方式,而是塑造着新的生活方式。机械钟就是典型的例子,它推动着“看时间”的需求,重塑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直到工业革命之后,“看时间”不再只是修道士等少数人群的需求,而开始成为所有人的需要。所以技术史家芒福德讲,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与其说是蒸汽机,不如说是时钟。
习惯于“看时间”后,人们更倾向于以视觉而不再是听觉,来感受时间的存在。麦克卢汉认为,这正是视觉中心主义对古老的声觉-触觉空间的瓦解。视觉突出了时间的客观性和均匀性,而消解了其遭遇性和突然性。麦克卢汉甚至主张,这种受时钟和印刷机强化了的新感知方式,决定了现代科学抽象化、对象化的思维方式,也决定了现代人冷漠化、个人主义的生活态度。
在今天,机械钟逐渐退隐了,我们生活节奏的最新支配者是手机,而手机的屏幕上最显眼的往往还是“时间”。随着技术的进步,我们仿佛能够越来越精确和自主地控制时间,我们能够把闹钟定到7点59分或8点01分,仿佛控制权很强了,但9点上班可是身不由己啊。我们的技术越来越精细地控制着时间,而我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深地被技术所主宰。
(选自《什么是技术》)

